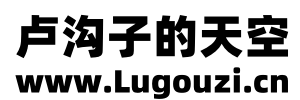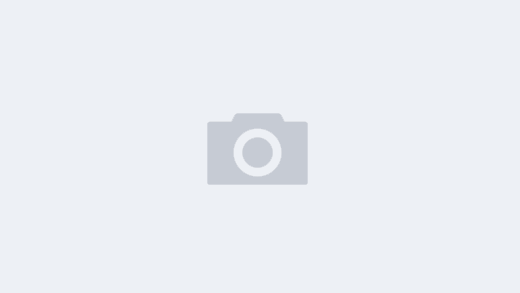脚炉之忆
我小时候冬天的御寒神器,晚上被子里有汤婆子,白天脚下有脚炉。一个人的脚因远离心脏故而是全身最冷的地方,所以有脚冷冷到心,脚暖暖全身之说。脚炉,较之高堂大户的香炉、文人雅士书房的香薰炉、钟鸣鼎食人家的掌中的手炉,是最具民间烟火气的一种御寒铜炉,一般直径约16~22cm,高10~15cm,在寒冬腊月滴水成冰的日子里,犹如室内的供暖神器,正可起到暖脚暖心的作用,因而深受人们的喜爱。
脚炉是烘脚用的炉子,有铜质、铝质和铁质几种类型。它有炉襻、炉盖、炉身、炉耳组成;造型有八角形、花篮形、南瓜形、方形、腰形等;上有盖,下有底,一个拎襻在中间;盖子上有一个个百孔千疮密密麻麻蜂窝状的气孔。有个谜语说:“矮卜素(“卜素”是谐音),眼睛多,吃红饭,拉黑屎。”谜语极其形象地描绘出脚炉的外形和功能。那时每天烧好晚饭,母亲都要倒掉昨日脚炉里的灰烬,加上砻糠或木屑,然后从灶肚里扒一些尚未燃尽的草木灰,拨进脚炉中约四分之三左右,再盖上盖子。少顷,从脚炉的洞孔里,就会暖气氤氲,并冒出一缕缕袅袅青烟,可闻到一丝丝烟味,捧在手里可焐手,放在脚下可烘足,揣进怀里能暖身。为了尽可能让它冷得慢些,母亲用稻草做了个脚炉窠,有了脚炉窠,除了保暖,脚炉不直接放在地上,能让脚炉保持干净,而且可以延长使用寿命。有脚炉的地方,就有人间的温暖;有脚炉的房间,就会温暖如春。
遥想当年陶潜,冬日里壶无余沥,灶不见炊烟,冻得只能晒太阳。他的《咏贫士》云:“凄厉岁云暮,拥褐曝前轩。”这位“贫士”也许就是诗人自己吧。杜甫也不例外,他的《西阁曝日》云:“凛冽倦玄冬,负暄嗜飞阁。”他也没有脚炉,只能呵手驱寒,以负暄来抵抗寒冷了。
脚炉发展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庶几成了艺术品和实用品的完美结合。不仅形式上有大大小小、高高低低、扁扁圆圆之别,还有的在脚炉盖上也充满了诗人与画家的遐思玄想:那些密密麻麻的气孔,錾刻着菱形、梅花形、蝴蝶形等的图案;有的甚至整个盖子上就是一幅雕镂精致、线条流畅、栩栩如生的风景画或仕女图。还有提柄上,设计成花纹柄、扭丝柄等造型,成了形、艺、韵、意俱佳的艺术品。
在昔日严寒地冻的日子里,阙如御寒的器具,更无裘衣重裹的条件,当时有些家庭的瓦房、草房,甚至自己搭建的“草棚棚”,住房的保暖条件颇糟,窗缝、门缝、墙缝、瓦缝等各种缝隙处,都可以灌进冷风,如俗话说的,没有不透风的墙,朔风砭骨,故而在房间里还能听到西北风“呼呼”的啸叫声,所以尽管穿着老棉袄、老棉裤、老棉鞋、棉背心、棉帽子、棉手套;犹冷得瑟瑟发抖,抖到可以听见自己牙齿打颤的“嘚嘚”声。当时我的手上冻得红萝卜似的并生满了冻疮,像烂柿子一样;有些地方还裂出一道道渗血的口子;有时刮了一夜风,我流了一夜的鼻涕,这“一夜风流”像关不住的水龙头。当时要有一只脚炉,就像费翔演唱的:“你就像那冬天里的一把火”无冻馁之忧,该多好、多暖、多舒服啊!烘得冻疮发痒,烘得两脚出汗,烘得整天不肯放手,拥衾而卧,高枕无忧。当时白天,人们围坐在脚炉旁边,将脚靠近脚炉取暖。有不少家庭妇女,一边脚上烘着脚炉,一边手中忙着针黹女红,取暖干活两不误。
脚炉不仅取暖,还有烘干器的作用。有婴儿的家庭,常常要烘尿布,烘湿漉漉的尿床被单;在没有太阳的日子里,有时要烘鞋烘袜烘衣物等等。为防止脚炉散热快,有人家买来脚炉窠,将脚炉“窝”在窠里,起到一定的保温作用。
如今各种取暖电器如雨后春笋:电热毯、电热器、暖风机、暖手宝、暖炉、油汀、空调等,走进了千家万户,从而,昔日与我们朝夕相伴、度过寒冬腊月的汤婆子、脚炉等,也就渐渐而悄无声息地退出了历史舞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