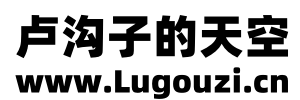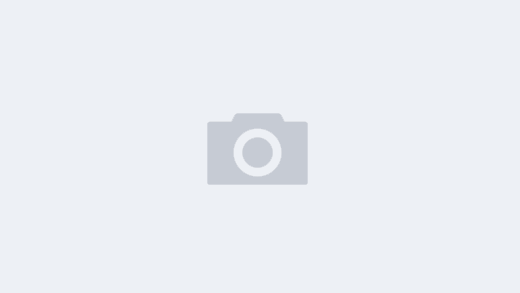潮声总在黎明前叩响窗棂。那时我总以为大海是位爱赖床的旅人,趁着天未亮透,将昨夜晾在礁石上的星星一枚枚收回锦囊。祖母补渔网的银梭在晨雾里穿梭,针脚织进咸涩的海风,织成我童年的第一缕晨光。
木屐踩过被露水浸润的沙滩,会惊起一串透明的脚印。退潮后的滩涂是座露天博物馆,招潮蟹举着不对称的螯足在泥地上写甲骨文,海葵在石缝里绽放成永不凋谢的蓝莲花。我总把拾到的贝壳贴在耳边,直到某天突然听懂了它们的秘密——原来每片螺旋纹路里,都藏着一座会呼吸的迷宫。
正午的渔村是慵懒的。晒盐场的白结晶在日头下闪着细碎的银光,像谁打翻了装满星屑的陶罐。父亲撒网时手臂划出的弧线,总让我想起屋檐下晾晒的弯月。渔网坠入海面的刹那,无数银鳞跃出水面,像是大海突然翻开了珍藏的童话书。
最妙是暮色四合时分。归港的渔船载着摇晃的夕阳,桅杆上晾晒的渔网滴落金红的水珠。我们蹲在灶台前烤小银鱼,火苗舔舐着海货的鲜甜,将咸香的气息揉进晚霞。祖父用海螺壳当酒杯,啜饮的姿势庄严如某种古老仪式,直到檐角的渔灯次第亮起,在浓稠的夜色里游成发光的鱼群。
而今站在玻璃幕墙前俯瞰车流,总错觉那川流不息的尾灯是搁浅在都市里的粼粼波光。某个加班的深夜,忽然在文件堆里嗅到若有若无的咸腥——原来记忆早已将那片海腌渍成琥珀,每当心潮涌动时,便有细沙从指缝间簌簌漏下。
潮涨潮退二十载,我终究明白,有些年轮是海水刻就的。就像祖母补网的银梭永远悬在晨雾里,父亲的渔网始终盛着半兜星光,而那个赤脚追浪的孩子,永远站在涨潮线上,等待下一朵浪花带来深海的耳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