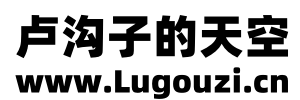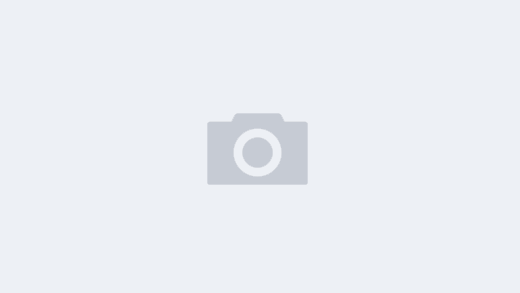厂区最后一盏钨丝灯熄灭那晚,我的扳手在工具箱里生了红锈。月光淌过车床的沟槽,铁屑堆成的山丘在阴影中坍缩,像被抽走脊梁的巨兽。
粮本上的蓝戳越来越密。妻子把酸菜缸挪到阳台上,腾出地方糊火柴盒,纸壳划破的伤口总也赶不上结痂的速度。女儿把铅笔用到只剩拇指长,橡皮擦成了薄片,她蹲在锅炉房废墟里写作业,雪粒落在发烫的钢锭残骸上,咝咝作响。
老周头把翻毛皮鞋换成胶靴,每天四点去早市支煎饼摊。他总多给我撒一把葱花,”钢厂舌头就爱这口焦脆”,铁铲刮擦铁板的声音,恍惚是当年浇铸钢模的沙沙响。我们这些”老伙计”常蹲在马路牙子上,用搪瓷缸分饮散装白酒,看蒸汽从下水道井盖喷出来,像极了从前淬火池的白烟。
腊月二十三祭灶王,妻子从红绒布里取出下岗证垫桌脚。窗外冰溜子把月光折成七彩,女儿忽然指着说:”爸,这多像你从前熔的钢水花。”她睫毛上沾着面粉,正帮母亲包破边露馅的饺子。
货运站招临时工那天,我摸出工具箱最底层的帆布手套。霜花在毛线缝隙里结晶,掌纹间藏着的铁腥味忽然苏醒,恍惚听见行车铃在冻云深处摇晃。妻子往我饭盒里塞进两个烤土豆,滚烫的,像两颗重新跳动的心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