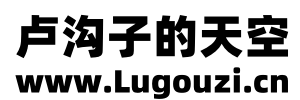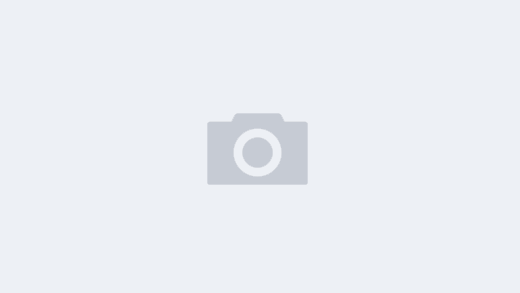青石板路是老街的琴键,清晨上学的脚步声踩出梆子戏的韵脚。早市豆浆的雾气裹着晨曦升腾,炸油条的竹筷在油锅里划出金色五线谱——那是我们心照不宣的开场白。
邮局拐角的绿漆门总让我想起薄荷糖,铜信箱的投递口含着来自远方的只言片语。柜台后的老郑叔戴着玳瑁眼镜,分拣信件的动作像在整理陈年茶叶,连空气都染上了宣纸的沉香。我常偷看母亲取汇款单时微颤的睫毛,那些皱巴巴的纸片上洇着父亲在异乡的汗渍。
供销社的玻璃柜台里躺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童话。搪瓷脸盆上的红双喜总对着新到的的确良布料傻笑,铁皮饼干桶开合时发出的叹息,惊醒了货架顶端打盹的灰尘。最馋人的是爆米花机开炉的轰鸣,白胖的米粒炸开时,整条街的童年都屏住了呼吸。
黄昏的中学操场是褪色的胶片。煤渣跑道吞噬了太多秘密,单杠上晾着被风干的青春期。老班长的二八单车后座永远空着,车铃铛却在某个暴雨天突然哑了嗓子。我们传阅的琼瑶小说里,总夹着从《青年文摘》上撕下的诗句,那些潦草的笔画比代数公式更让人脸红。
夜市的煤球炉点亮后,整条街开始分泌温暖的酶。修表匠的台灯把时间切成薄片,烤红薯的香气勾着晚自习归来的饥肠。录像厅门口的霓虹灯管漏了光,港片里的枪声惊飞了电线杆上的麻雀。母亲织毛衣的竹针还在窗棂下碰撞,毛线球滚过的地方,月亮就圆了一圈。
如今在高铁站望见相似的绿漆门,恍惚又听见老信箱吞咽信件的声响。手机导航提示右转时,鼻尖突然窜过煤炉上煎药的苦香——那些嵌在县城褶皱里的光斑,原是用冰糖葫芦的琥珀色浇铸的。当写字楼格子间漫起秋雾,我仍能摸到裤兜里那颗化了形的薄荷糖,棱角温柔地硌着掌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