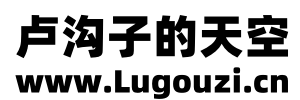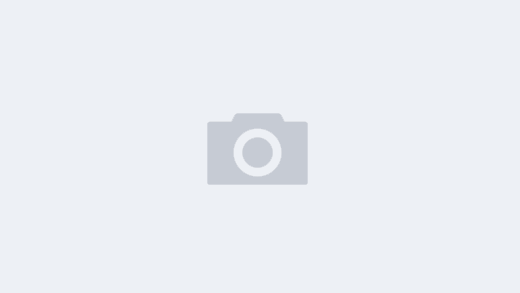清晨五点,机床厂的更衣室还亮着第一盏灯。我摸着工作服上洗得发白的”三级车工”胸牌,那些和铁疙瘩打交道的岁月就像车刀卷起的铁屑,在记忆里闪着银光。
1978年的冬天,我缩着脖子钻进崇明农机厂。师傅老周握着游标卡尺站在C620车床前,车刀与45号钢接触的刹那,橘红色的铁花在阴冷车间里绽开。”手要稳,眼要准,心要静。”师傅的训导声混着机床轰鸣,在我耳边响了四十年。记得第一次独立加工法兰盘,因为看错小数点车废了三个毛坯,师傅罚我举着卡尺在车间站了整上午。现在想来,那游标上0.02毫米的刻度,分明刻着匠人的尊严。
九十年代厂里引进首台数控车床时,全车间老师傅都成了哑炮。我连续三晚蹲在控制柜前,对照着日文说明书画满三大本笔记。当显示屏亮起绿色坐标轴,刀架在伺服电机驱动下跳起精准的华尔兹,我忽然明白,老手艺不是枷锁而是翅膀。就像熊朝林师傅攻关微分进刀系统那样,我们把千分表架在机床上,用0.001毫米的执着对抗着”中国制造”的偏见。
这些年带过的徒弟里,最灵光的小杨去年得了”上海工匠”称号。他设计的多功能组合夹具申请专利那天,我摩挲着那沓图纸,仿佛触摸到时光的温度。现在的年轻人总说智能制造,却不知再先进的五轴加工中心,也要懂车刀角度、懂材料脾气。上个月在车间看见新来的实习生戴着AR眼镜编程,我默默把四十年前的磨刀石放在了他工具箱里。
退休前最后一件作品是为长征火箭加工燃料阀体。当三坐标检测仪显示所有公差都在μ级以内,我摘下老花镜,在检验单上签下第36820个合格标记。走出厂房时,夕阳把龙门吊的影子拉得很长,就像我留在机床导轨上的那些年轮。这一辈子,车刀削去了青春,却车出了中国制造的脊梁;铁屑染白了双鬓,却铸就了时光淬炼的勋章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