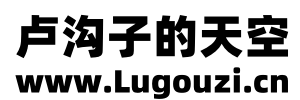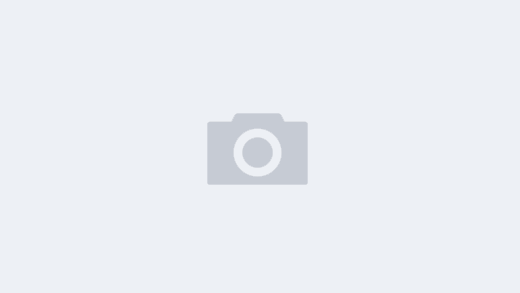雪粒子砸得玻璃窗沙沙响时,窗缝里的冰棱总会长出一寸。我蜷在火炕最暖的角落,看母亲把新渍的酸菜码进瓦缸,咸腥的水珠从她冻红的指尖滴落,在青砖地上洇出深色的圆斑。
城东铁匠铺的烟囱最早醒。天还青着,老张头已经踩得风箱呼哧作响,铁砧上火星子四溅,烧红的镰刀浸进冷水时腾起白烟。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常蹲在门槛上,等那柄铁勺舀来滚烫的糖稀,在青石板上画糖画——总也画不成龙,倒像条胖头鱼。
菜窖里的冬储最是神奇。白菜码成金字塔,蒙着霜的苹果挨着黄澄澄的倭瓜。父亲用草绳捆住我的腰,把我吊进地洞取腌萝卜。泥土的腥气裹着霉味,手电筒光束里浮动的灰尘,恍惚是另一个星系的银河。
西街澡堂子每逢周末便雾气蒸腾。大池子里的水泛着铁锈色,老孙头搓澡的丝瓜瓤刮过脊背,疼得人龇牙咧嘴。女浴间总传来婴孩响亮的啼哭,混着妇人们家长里短的嬉笑,水汽将人声揉成温软的絮团。
开春头场雨后,供销社墙根的冰溜子开始滴水。碎花窗帘在穿堂风里起起落落,隔壁赵婶送来新蒸的粘豆包,白瓷碗底还粘着去年秋天的红豆沙。父亲蹲在门槛修自行车,车铃铛丁零当啷响,震落了檐角最后一片残雪。